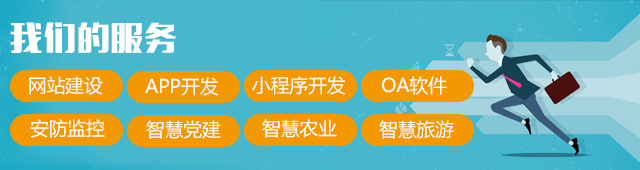山 外 山——崔振宽的意义
张 渝
摘 要:从“山外山”的意象入手,借助刘骁纯“黄崔系统”,探讨崔振宽焦墨山水的存在价值以及“黄崔系统”的创生与衍生,进而指出“山外山”的文脉意义。关键词:黄崔系统;山外山;崔振宽
崔振宽丨 陕西长安人,1935年生于西安,1960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现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美术家协会顾问、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陕西国画院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作品参加第六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百年中国画展,首届和第二届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获艺术奖),中国当代艺术欧洲巡回展,向祖国汇报——新中国美术60年展,中国美术60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中国艺术大展,联合国世界公务员日中国艺术大展等。1994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2002年先后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成都现代艺术馆、江苏省美术馆举办气象苍莽·崔振宽山水艺术巡回展。2005年举办从艺五十年·崔振宽山水艺术回顾展,2010年在杭州举办水墨长安·崔振宽06—10新作展,2015年、2016年分别在中国美术馆和西安崔振宽美术馆举办苍山无言——崔振宽画展。200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对其艺术成就进行专题报道。2007年获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造型艺术奖提名奖。出版有不同版本的《崔振宽画集》多种。
数十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等学术机构收藏。被列为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研究课题“山水卷核心画家”及“中国画当代艺术30年”课题重点研究艺术家。
崔振宽丨又上华上之一丨209cm×126cm丨纸本焦墨丨2019年
人生很短,短得只有相爱的那一点点。
这句诗很妙,也很艺术,但它表述的只是人生某个真实的触点,而不是全部真相。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因为触点的真实,而相信触点本身就是人生真实的全部?显然不能。遗憾的是,我的一些朋友还真是把局部的触点放大成想象的整体真实。这种充满善良和真诚,甚至不无诗意的想象,在他们对于崔振宽艺术的评价中,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崔振宽两次重要画展的策展人殷双喜和王林都从“山”的维度来思考展览主题。他们二人为展览的命名分别为《气象苍茫》和《苍山无言》。这样的命名也的确凸出了崔振宽在当代中国山水画坛作为“山”的意义。但是,在画展研讨以及随后的传播环节,作为山的形象的崔振宽,却在各种术语的删节下,简化为一棵树。于是,抽象、表象,焦墨、水墨等术语,便如枝如叶地展示了崔振宽作为一棵树的形象。
然而,人生很短,短的经不起一点点的误读。
应该明白,一棵再大的树,哪怕其遮天蔽日,也依旧只是一棵树。但一座山,即使是一座很小的山,也可以生长很多的树。因此,如何看见一座山,而不是抚摸一棵树,也就成了我们理解崔振宽艺术的一条红线。而这也恰恰是我强调“山外山”命名的根本原因。
在我的眼里,《气象苍茫》《苍山无言》类的命名,对于崔振宽艺术形象的定位,不是不可以,而是容易让人偷懒,把一个持续的、深层的学术课题简化为一次性的学术绿化。
崔振宽丨古镇之二丨246.2cm×121cm丨纸本焦墨丨2018年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探寻一座山?
刘骁纯曾写过三篇重要文章,分别是:《蒋兆和与“徐蒋系统”》《吴冠中与“林吴系统”》《崔振宽与“黄崔系统”》。前两个系统已有公论,不必多言,需要讨论的是第三个系统。在讨论第3个系统时,刘骁纯写到:“改革开放以来,黄宾虹的门徒如潮,颖出者唯崔振宽一人。所谓颖出,指的是在关联中完全独立并达到一定水平,唯其如此才可以称为’黄崔系统’。我的意思是,虽然崔振宽在艺术境界上与黄宾虹还有一定距离,但就其目前的成就以及所提出的问题,可以以’黄崔系统’为基本思路来考察他的艺术。” [1]
刘骁纯是如何考察的?
他首先界定黄宾虹课题三大趋向:“(1)解体山水;(2)笔墨自主化,大写意;(3)其笔墨属文人山水画正统的书法用笔的笔墨系统。”
其次,刘骁纯谈论崔振宽进入黄宾虹课题的历史意义:“(1)进一步解体山水;(2)进一步突出笔墨,继续发展大写意;(3)坚持文人山水画正宗的书法用笔的笔墨系统;(4)探索黄宾虹未曾探索的结构自主化。四点之中,第三点是内功,第二、四两点是主攻方位,第一点是不期然而然的外显效果。因此,传统笔墨功夫不达到一定的层面,不可能接近黄宾虹课题。”[1]
刘骁纯还从崔振宽本人的论述中解释崔振宽迈入焦墨的心理动因是对苍浑和力度的一贯偏爱,“’以焦墨表现西北的自然风貌似乎更加贴近’;其文化动因是对文人画的深刻反省:他们在笔墨’形式’探求取得高度发展中消弱或丢掉了’汉唐之风’的气度,在追求’书卷气’的高雅格调中,脱离了’粗俗’的民间艺术强大的生命力和丰富滋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禁锢了文人画自身,其影响所及,直至现在。”[1]
崔振宽丨华岳后山印象丨138.3cm×70cm丨纸本水墨丨2018年
通过刘骁纯抽丝剥茧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崔振宽进入黄宾虹课题之后,如果没有其后期焦墨系统的开创,他可能只是一名优秀的山水画家,而不是成其大者。
非常佩服刘骁纯关于崔振宽艺术的定位:“黄崔系统”。黄,指黄宾虹。作为中国山水画史上的一座高峰,黄宾虹的艺术形象以及艺术史地位已被公认:山。而刘骁纯把黄、崔并举的事实本身,也告诉我们,崔振宽是一座山。一座和黄宾虹有关,却有别于黄宾虹的另一座高峰。基于此,为了更明确地标识出崔振宽的艺术谱系,我提出了“山外山”的命题。如此命名的目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黄崔系统”命名,我们可以说,黄宾虹是内山,崔振宽是外山。内山,外山,相互关联,也相互独立。他们各自的独立,不用多说。但黄对崔又是如何影响的?安德烈·纪德说:“影响不创造任何东西,它只是唤醒。”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黄宾虹唤醒了崔振宽,并使之和自己以山脉的形象绵延成中国山水画的“横断山脉”。
第二、作为山脉中的一座山峰,崔振宽可以用自己的艺术存在,告诉所有自以为是、浮夸、徒有5A景区之名的当代画坛上的山头们:山外有山。自然,“山外山”,也可以是一种理性的宣言:作为真正的艺术家,崔振宽理性地知道“山外有山”,因而更加清晰自己当下的位置和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三、“山外山”的词义组合本身,也是中国诗性文化的一个诗意承续。为什么这样说?宋代范温在其《潜溪诗眼》中说,他的一个朋友从黄庭坚那里看到了一个“韵”的概念,就跑来和他探讨什么是“韵”。朋友先后列举了潇洒、简练、生动、不俗等几个概念,范温都一一否决后说,“韵”,就是“有余意”。我关于“山外山”的命名本身恰恰强调了这种“余意”。这层意思也是刘骁纯《崔振宽与“黄崔系统”》一文忽略的一层意义。
崔振宽丨秦岭残雪丨178cm×474cm丨纸本水墨丨2012年
“山外山”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崔振宽作为一座山峰的美学依据。
关于一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角度、立场不同,对于同一座山的理解与判断也不同。从风骨、雄浑、苍茫等美学范畴中,我们都可以解读崔振宽艺术。而这种可以多角度解读的事实本身,又反过来从语言和意义的丰富性上证明了崔振宽这座山的存在。
我们知道,一座山,尤其是北方的山,其最基本的美学品性便是“雄浑”。雄浑之外,还会有秀美、险怪、苍翠、苍茫等形态,但这些对于山来说不是根本性的,而是枝叶。所以,我从“雄浑”进入一座山的美学考察。在雄浑这个范畴内,我们可以看到黄宾虹和崔振宽的一个共同点:一心定而王天下。不同的是,黄宾虹走向浑漫,若水之流;崔振宽走向雄壮,泰山横卧。他们二人的艺术历程不是没有阶段性的变化,而是他们的所有变化,都是基于自己艺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而非时风。在“吾道一以贯之”中,崔振宽艺术特点非常明晰地表现出来:梗慨多气,笔力雄壮,气象苍茫。
雄浑之外,崔振宽的苍茫气象中,还内蕴着黄宾虹艺术作品中没有或说少见的生命质色:苦涩。我在以前所写的《审苦范式中的崔振宽》一文中,曾经如此写道:崔振宽对于长安画派的当下拓殖,对于黄宾虹笔墨符号的现代延展,是有目共睹的,否则,评论家们不会不吝啬笔下的词汇,比如雄阔、壮美、浑厚、博大、精深。问题是,当所有这一切都在崔氏作品前成了事实上的陈词滥调时,那么,陈词滥调所指陈的事实又是基于何种生命质色?或者说,这一切的文化本根又是什么?思来想去,或许只有“审苦”二字。
崔振宽丨华岳之皴图一丨247cm×121cm丨纸本水墨丨2019年
当然,崔振宽的作品也经常地施以墨绿、赭石等色,但其作品的总体本色却是黑压压的沉默。因了这种黑压压的沉默,我悄悄窥到了崔氏作品所内蕴的、悲苦的生命质色。它可以是荒瘠的西北地貌的景观内射,也可以是发自肺腑的悲天悯人的诗性之思。他在亢奋而又沉郁的笔墨基调和极端化的叙事方式——满构图中,悄无声息地展示了“悲苦”二字。并由此开始了对传统的反判以及对现代的链接,这也是崔振宽的笔墨越来越抽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然,苦难或者恶劣的西北地貌并非西北画家所独有的叙事资源,然而,衡诸画坛,也只有在西北画家那里,恶劣的地理环境以及由之而来的苦难意识才真正地成了一种内在的精神高度。也只有在这里,我才能理会袁枚批评钟嵘《诗品》时说的一句话:“只标妙境,未写苦心。”顺着这句话,我要说的是,江浙画家的主体风格是审妙,而西北画家的主体风格是审苦,两种风格不存在高低之分,却有大小之别。审妙一路的画家多精品,少大品;审苦一路的画家则多大品、少精品。作为美学范畴,审苦并未以独立的形态或语辞隆起在美学史上,但是作为一种创作意识,在俄罗斯艺术家,在袁枚那里,却恒久存在着,它不是一个新的话语空间,而是今日的我们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次语言去蔽。去蔽之后,这个并不算新的空间也就成了我们探索新的可能的话语空间。它也因之成了一种新空间。
另外,为什么“苦”让人记忆深刻,而“甜”却容易让人忘记?因为,“苦”在五行中属金,易沉淀。而“甜”属木,走肝,易挥发。这也是苦难常常让人深刻的一个理由。当年的长安画派以及当下西北画家的艺术创作,之所以标举大品,并时有大品产生,其根脉上的审美经验以及审美追求,也大都与此相关。自然,崔振宽艺术之所以可以“雄不以色,悲不以泪”的根源,也在这里。
较之传统山水画,崔振宽的作品已然具备了前卫品性,却不是真正的前卫。因为,就表现形态言,前卫艺术讲求独创、反叛、不可重复。崔氏作品尽管也一定程度地具备独创、反判的因子,却不彻底,他的出发点是文化根脉的传延,而非空所依傍的现代幻想。当他把传统笔墨的“点”延展为“线”,又把“线”浓缩为“点”时,并不是玩弄朝三暮四的把戏,而是探寻一种新的可能。在我看来,崔振宽的重新出发既是笔墨符号意义上的,也是视点图式意义上的,而后一点,又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崔振宽丨华山卧游图一丨247.5cm×123cm丨纸本水墨丨2019年
传统文化中,“观”,不止是“看”的方式,而且是心绪漂摇中的“目”之游。崔氏的智性在于具体创作中,追求远观与旷观的同时,并不排除“见”的局部精微。如果说,“观”是指整体性的看,“见”是指局部的看的话,那么,崔的作品在追求整体性的远观与旷观中,又锲而不舍地在“见”的局部上施展传统笔墨功夫,在“观”与“见”的有机组合中,崔振宽的山水画基本完成了这一转变;由传统的精微的笔墨功夫转求当代美学仪式震惊的美学效果,这一转变帮助崔振宽异常尖锐地切入了苦难本源。他在构想的心理自然中置身苍莽之境,然后追求不无崇高、壮美的生存命运,追求审苦意义上的价值实现,而这恰恰是崔振宽为代表的艺术家不是农民却又搂着农业文化格局不放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农村或农业文明也如同传统的笔墨程式一样,它既是一种符号,也是一种工具,它静静地待在那里考量着每位艺术家的智性空间,对此,崔振宽以其超人的智性构筑了“黑压压的沉默”,至于沉默之中有多少精灵,画家没说,他有意地藏匿她们,让我们惊奇而又静默地思,然后在他雄浑的作品中和他一起不无神秘地出发。
冯至说里尔克从青春走入中年的过程中,有一种新的意志,“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岳”。这是极富创见的言说。事实上,崔振宽的艺术创作中,也有这种“新意志”的产生:转向,由水墨转向焦墨。因为他的转向中,水墨和焦墨交互缠绕、往复向前,以至于有了关于崔振宽作品究竟是水墨的好,还是焦墨的好的争论。
崔振宽丨华山绝顶丨137.7cm×69.8cm丨纸本水墨丨2018年
不想更多地介入这些在我看来并无太多意义的争论。我只想说,从古代已经逝去的画家到现在依然健在的焦墨画家阵营里,哪一个画家的焦墨作品可以好过崔振宽的?没有。无论是明末清初的程邃的焦墨,还是以焦墨名世的张仃,他们的焦墨作品在语言表达和焦墨技术本体的丰富性上,都没有抵达崔振宽的高度。苏轼《评韩柳诗》中有段话,非常适合评述崔振宽的焦墨。苏轼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诗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
无独有偶,皮道坚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中的画学个案——崔振宽的焦墨山水》也曾做过意义上与我相近的表述。他说:“进入新世纪以来,崔振宽已经基本确立了他的焦墨山水在中国山水画笔墨系统中的意义。通过焦墨,他比任何一位前辈都更鲜明而有效地使山水画中的’骨法用笔’具有了某种相对纯粹的抽象性,那些几欲脱离画面的或厚重、结实、硬挺,或松活、苍老、遒劲的线与点,犹如交响乐中铿锵有力、跌荡起伏、错落有致的音符,其诉诸听觉的意义有时甚或凌驾于整个交响乐的主题之上。”[2]
刘骁纯曾感慨说:“’由旧翻新’比’弃旧图新’艰苦得多。’由旧’就是以文人山水画的传统为创作的基础和根由,这方面的学养和功力的积累好比望不到尽头的天涯路;而’翻新’又被理论家宣布为’穷途末路’,前景渺茫得很。因此,不论口头上是如何说的,在实际上埋头走这条路的人十分稀少。”[1]
在这条人迹稀少的路径上,崔振宽“由旧翻新”的是什么?
在刘骁纯看来,崔振宽是在黄宾虹课题中完成了弱化山水意象并转型半抽象山水。在崔振宽2018年底最新创作的《华山图》中,我们已看不到具备形象可辨识度的华山,但你知道华山就在那里。它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情绪或者气质型的现代气息。很多人都在谈论笔墨的现代性以及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但什么是现代性?抽象或半抽象之外,崔振宽的焦墨山水是否还有现代性?
崔振宽丨又上华山之四丨210cm×126cm丨纸本焦墨丨2019年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675年-1075年),中世纪(1075年-1475年),现代时代(1475年-1875年),后现代时期(1875年-至今)。他划分的“现代时期”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而他所认为的后现代时期,即是指1875年以来,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动乱年代”。
汤因比是在与中世纪的区分中呈现出现代意义的。如果说“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那么,崔振宽目前的焦墨创作中最具前瞻意义的是他通过平面化、符号化以及抽象化的艺术努力,把写生式的传统艺术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语言方式。崔振宽“脱域”之后,其笔下传统的地域风格变得恍兮惚兮。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使其创作很难如其早期作品那样可以具体指认秦岭某个山头、某处地段,但另一方面,又使其作品在不可辨识的恍兮惚兮中,有了更大的“混沌之象”。有意味的是,这个“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象”,而是抽象之象。故此,“脱域”本身既是崔振宽的一种批判态度,也是他在黄宾虹系统之外自成体系,进而成为“山外山”的现实表现。
“脱域”之前的“山”和“脱域”之后的山,表面上不是一座山,但内在血脉上一以贯之,一如“黄崔系统”中的“内山”与“外山”。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崔振宽自己作品的不同分期而形成了他自己的“山外山”系统。
崔振宽丨河谷之一丨124.9cm×248cm丨纸本焦墨丨2017年
在“由旧翻新”的笔墨现代中,我们不能忽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骨法用笔”。在这方面,皮道坚的论述值得重视。他说:“谢赫最初提出’骨法’一词时可能主要是’拟画于人’,人有’气韵’与’骨相’,画也亦然,并不曾想到书法性的内涵;张彦远则可能仅在强调书画用笔同意而非同法;直至赵孟頫才首次对’书画用笔同’进行了技术性设定;倪瓒所赞赏王蒙’王侯笔力能扛鼎’,其实无半分强调用笔中金石气象之意味;董其昌等确立文人笔墨系统时,对宋代李公麟作品的篆籀气息只字不提;金农、吴昌硕等将金石书法引入绘画,于南宗正统美学而言毋宁说是一种反动与破坏;直至黄宾虹才真正将金石意味融入了温文尔雅的南宗笔墨,使得’骨法用笔’具有兼备文雅而温和、高古而雄强的中庸意味。就崔振宽而言,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作品的平面化倾向,跟上述专注于焦墨与骨法用笔的做法,显然都出自有意与黄宾虹拉开距离的尝试。具体地说,这种平面化处理就是将中景甚至远景拉近、放大,弱化山、树等物象的形体特征,同时加强焦墨点皴层次,形成凝重雄浑的视觉效果。在2012年11月接受记者采访时,崔振宽自称是追求’松散的结构’,而非’团块的结构’。”[2]
崔振宽丨秦岭大壑图丨258.5cm×620cm丨纸本焦墨丨2014年
皮道坚的这段梳理还是至关重要的。崔振宽的焦墨创作中最根本的还是骨法用笔。也正是在这一基点上,崔振宽依旧是传统文脉意义上的画家,属于刘骁纯概括的“黄崔系统”。但他不完全等同于纯粹文脉意义上的画家。他既在“黄崔系统”内,又在笔墨抽象性与平面化等方面超越了“黄崔系统”可能带有的系统内艺术风格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刘骁纯自己概括的“徐蒋系统”中十分明显。在摆脱了“徐蒋系统”的模式化以后,“黄崔系统”最可贵的意义就在于它不是如“徐蒋系统”那样显示系统的一致性,而是主要显示这个系统在形态学意义上的差异性。这种求异而非求同的差异性使得崔振宽的焦墨创作同时获得了传统水墨和现代水墨两大阵营的认可。这也是崔振宽的作品时而出现在传统型水墨展览上,又时而出现在现代水墨展览上的原因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主要由崔振宽引发的“黄崔系统”的内在差异性,使得崔振宽作品同时具备了传统(骨法用笔)与现代(抽象、平面、符号)双重身份。而这种身份本身再次形成“山外山”意象——传统是“内山”,现代是“外山”。
崔振宽的焦墨行乎所当行,止乎所当止。不拘于法,不越于法。他的作品在“骨法用笔”中延续着中国艺术的文脉,又在半抽象、平面化、符号化中无限接近现代艺术的内在品质,把很多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做到可能。应该知道,真正的现代性,不是一个历史时期而是艺术气质。
诗人说,历史是一则手写的故事、一串旧文字,任人诠释、组织。文论界也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说。其实,这些都不是历史的任意,而是经典的意义。无论作为话题,还是课题,崔振宽都很难一言以蔽之。他是一座山,而不是一棵树。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兴奋,并滔滔不绝。
夕阳山外山。
注释:
[1]刘骁纯.崔振宽与“黄崔系统”//崔振宽画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2]皮道坚.中国当代思想史中的画学个案——崔振宽的焦墨山水//崔振宽画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藝術展覽|藝術收藏|藝術鑒定|學術研究|公共教育
西安崔振宽美术馆是由当代中国画重要代表人物崔振宽先生资助,陕西水墨长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一座集展览陈列、收藏保护、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公共教育、国际交流为一体的大型民营公共美术馆。
美术馆 2016 年建成开馆,座落于西安灞桥生态湿地公园,占地 38 亩,建筑面积 16000 平方米,设崔振宽作品陈列厅、综合展厅、艺术品典藏库、多功能报告厅、贵宾接待厅等展览应用空间。配套有艺术酒店、餐厅、艺术品商店、水墨长安艺术书吧、咖啡厅、停车场等设施,可举办不同类型的大、中型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
美术馆地处古都西安——是以周秦汉唐辉煌历史著称的世界文化名城,亦是古代亚欧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国家中心城市。崔振宽美术馆与同时建立的西安市水墨长安艺术博物馆一道,展示、收藏和研究高品质、代表性的历史文物、文人书画、民间工艺等中国传统艺术。
美术馆以三项学术工作为重点:一、展示、收藏和研究崔振宽先生艺术作品及文献资料; 二、致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的展览收藏和研究推广;三、推进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和国内国际交流的展览研究和收藏推广。
西安崔振宽美术馆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开放的文化态度、严谨的学术精神,努力打造传统性与现代性并重的学术型、知识型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公益性公共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