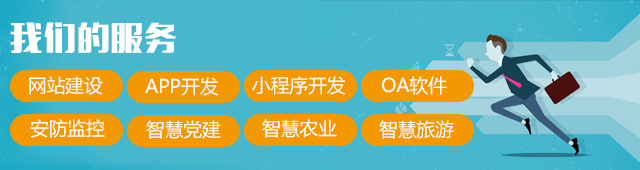1971年7月摄于果洛州大武河畔
编者按:
今年四月份以来,潘炜先生抽出了大量时间,将他在青海省军区政治部、青海省军区咸阳干休所、兰州军区西安翠华路第二干休所、中国农业银行西安分行、陕西长安书画研究院工作期间,在各种报刊、广播电台刊登、播出的新闻报道、通讯、散文、游记等数十篇稿件,进行整理,准备集结成册,出版发行。书名叫做《我看人生这些年》。
最近,他又抓紧为此书补充写作了数篇文章。今天在此,先刊登七千多字的《我骄傲,我曾经是高原骑兵》,让读者了解一下当年的骑兵生活,也在此征求一下读者意见,以便修改后,收入书中。
我骄傲,我曾经是高原骑兵
潘炜
1968年2月29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武装部在我们的入伍登记表上,盖上了鲜红的印章,我们西安市26中的王东成、张小宝、李长喜、霍探玉、潘国民、雒铁毛、翟寅山和我,八名同学的军龄就从这一天开始计算了。 3月6日,我们在含光路的陕西省卫校集中,并穿上了绿军装。 3月7日下午,我和西安市的入伍青年们,在西安西站乘上了西去的绿皮火车。 火车开出不久,接兵的干部便给我们发放了十一元的津贴费。由于我们穿的是普通的军裤,所以我们猜不到我们是什么兵种,只知道内地当兵的津贴费是六元钱,我们比他们多,我们去的地方不会太近。过了兰州,车还继续往前开。又过了大半天,我们在西宁火车站下了车。在车站广场集合时,我们才隆重的知道了我们是果洛军分区的兵。但是,那里由于大雪封山,道路堵塞,汽车无法行走,我们只好先住在西宁市的青海民族学院,进行新兵政治教育和队列训练。
3月25日,接到通知,说我们可以前往果洛了。26日一大早,我们和在西安社会上招收的几位新兵,以及陕西黄陵县的88位新兵、青海本省分到果洛的新兵一起,乘上汽车九团的解放牌大卡车,坐着自己的背包,面对面、背靠背,每辆车坐上30个人,正式出发了。政治教育时,接我们的祁干事,给我们讲了果洛的地理位置、人文、经济、特产,说得大家心里都痒痒的,急切地盼望着赶快到达我们部队驻地,因为那里是祖国的一个好地方。一路上,我们这些小年轻们豪情满怀,群情激昂,大篷车里谈笑风生,歌声不断。过了海南州州府共和县,虽然全成了石子路,但还算顺畅。过了花石峡,去往玛多中队的战友向西去了。过了昌玛河,达日、甘德和班玛中队的战友,也要与我们分手,向南继续前进。因为大雪封山,在这里等候多时的地方领导和干部,我们分区机关滞留的同志,也要在这一天,和我们分到独立骑兵连的新兵一起乘车,还要向东驶去,向果洛进发!
我们越往前走,海拔越高,气温越低。三月的唐古拉山,依然冰天雪地,零下30多度的气温滴水成冰。到了玛积雪山的三十里沟,道路封堵仍然十分严重。公路道班的工人们,接到命令,做好了用推土机为我们军车开路的准备。我们一到,马上都紧跟在推土机后面,他们推一段,我们走一段。因为,稍微动作慢了,大风就会将周围的积雪,又吹到路面上,看不出哪里是道路来了。走着走着,有一段路面,结冰十分严重,路面非常光滑,汽车开上去后,只见轮子飞转,汽车就是原地不动。接兵干部只好脱掉自己的皮大衣,铺在冰面上,以增加轮胎的摩擦力。我们全体人员也跳下汽车,一起用力,推着汽车前进。这时我们才感到,可能更大的困难还在后边等着我们,周围放眼望去,到处是皑皑的白雪,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我们汽车右侧是两三层楼高的雪墙,左边则是看不到底的万丈深渊,令人胆战心惊。迎面刺骨的寒风,像小刀子一样,狠狠地划着我们的脸庞,又堵得我们喘不上气来。我们呼出的热气,凝结在眉毛上、皮帽子上,瞬间变成了冰块。老天爷在这里真是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我们一路上兴奋的心情,一下子飞到了九霄云外。
在三十里沟中部,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由于我们的汽车行驶十分缓慢,走一走,停一停,又不能熄火,所以水箱里的水消耗太多,竟然被烧干了。这时,只见我们的司机,将雪块放在了铁桶里,点着了喷枪,在雪块上和桶帮上喷烤,但由于气温太低,烤了好长时间,也没化成多少雪水。实在无法,他急中生智,让我们全部下车,排着队对着脸盆撒尿,尿满一盆,向水箱里加上一盆,直到加满水箱,发动着了汽车,大家这才算松了口气。
车缓缓爬行到尼卓玛山的最高端,空气更加稀薄,我们坐在车上,手脚也冻得失去了知觉。这时,我们的战友潘国明,突然倒在了别人怀里,不省人事,叫也叫不醒。大家不免都吓坏了,不知所措,有的赶快抚摸着他的胸口,有的喂水,有的掐人中。后来司机停下车来,从别的车上叫来了随队医生,给他插上了氧气,注射了强心剂,他才慢慢睁开了眼睛,缓过神来。军医说,一小时前,另一辆车上的祁干事也因高原反应,发生了昏迷,他通过道班工人,已经给分区打了电话,让派救护车,到前边好走一点的路段来接应一下,先送他们尽快到分区卫生所,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三十里沟,三十里的路,我们竟然走了一天一夜。皮大衣铺路、汽车加尿、抢救战友,也成了我一生中,心里永不磨灭的故事。这也是我们当兵生涯中,对我们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我们都坚强的挺过来了。这条路,后来多少年就没有改变过。记得有一年,又是这地方雪堵封山,道路不通,七月一日,我们才看到邮电局刚刚送来的,刊有“元旦社论”的报纸。
从西宁到果洛州共625公里,我们竟然用了6天时间才把它跑完,直到3月31日晚上八点多,我们总算到了部队的驻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州府玛沁县(亦称大武),等候我们多时的独立骑兵连的老兵们,都跑来敲锣打鼓的欢迎我们。
到了连队,我们和青海本地的汉族和藏族战士们分在一起,开始了新兵训练。上午为“天天读”,主要学习毛选,下午为“天天练”,主要练习军事技术,如队列和射击、刺杀及马术等课目。学习骑术时,先是由老同志牵着马,我们骑上在操场上转圈。随后老兵丢开缰绳,由我们左手握住缰绳和马鬃,右手抓住马鞍子,左脚踩上马镫,练习“上马上”、“下马下”的动作。再后来,就由我们自己骑上马,一个接一个在操场上由慢行到快跑。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就有不少人从马上掉了下来,更别说后来骑上马,往几公里外的东倾沟跑了。路上,马挖起了蹦子,速度很快,几个新兵蛋子掌握不好平衡,眼看着都从马上摔下来了。我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在巷子里见到马车经过时,都离得远远的,生怕马撂起蹶子踢了自己。现在,我们穿上了绿军装,成了骑兵战士了,再胆小,再害怕,硬着头皮也得骑上去,绝对不能当胆小鬼和逃兵。逐渐的,每个星期六上午,全连120人骑着马,进行20公里的“压马训练”时,我们也就慢慢适应了。每次压马时,100多匹马的队伍,一匹马和一匹马相隔一匹马的距离,前后拉开也要几百米长,在州上的公路上,一字排列开来时,也是十分壮观威武的,每当这时,都能吸引许多路人前来观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光荣和自豪感,我们在心里说,我们骄傲,我们是高原骑兵!
潘炜在执行任务时,与自己军马的合影
人们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句话用在骑兵身上也是再确切不过了。骑在马背上,上山难,下山就更胆怯了。做为一名熟练的骑手,不仅要做到人马合一,而且还要有驾驭它的本领,这本领没有一两年的功夫是不行的,而光有技术,没有胆量也是不行的。现在想起来,不是穿着那身绿军装,也不会有那样的胆量。
马正常前进时,是分为“走马”和“颠马”的。“走马”即是左前腿和左后腿同时前进,是“一顺顺”,但骑上这样的马,人的上身比较平稳,比较舒服,而“颠马”则是左前腿和右后腿是一起迈步的,人骑到上边,上下颠簸,要不了多久就会翻肠倒肚,疼痛难忍。“走马”一般是连长、排长和班长骑的,战士一般都是骑的“颠马”。但不管什么马,骑的时间一长,我们的屁股都会被磨烂的。有时皮磨掉了,肉粘在衬裤上,揭都揭不下来。
骑兵,除了这些皮肉之苦外,随时随地也是有危险的。一次,我们连队压马训练时,副连长贾鸿郁和我骑着马走在最后,负责收尾。突然,藏民的一只藏獒,从远处冲了过来,一会儿跑到我们队伍前头,一会儿又跑到我们队伍的最后,使大家都十分紧张。忽然,它将贾副连长的马屁股咬出了一道血口子。贾副连长的红鬃马,仅次于连长和指导员的军马,全连排列第三,个子高、腿长、腰子细,既是一匹俊马,更是一匹烈马。它被藏獒偷袭受惊后,前蹄腾起,四处狂奔。这时,贾副连长一手拉住马缰绳,一手拍着马脖子,同时两腿紧紧夹住马肚子给马安慰,稳定它的情绪。但藏獒却穷追不舍,张开血盆大口,再次向马屁股扑去。但它这次十分不幸,牙齿挂在了马尾巴的毛上,脱不了身,直到不停的翻滚而被拖死。藏獒是藏民的看家宝,藏民知道后,几个人追到了我们连部要求赔偿。我当时已是连队的司务长了,我们尽管没有任何责任,但因为怕影响军民关系,几个人反复给藏民做工作,并给他们每人送了一块他们最爱喝的,四斤重的湖南益阳茯砖茶后,才算了结。
战马是一种特殊的马,它有不甘落后、勇往直前的品质和精神。它是随时要参加战斗的马。所以我们平时要对战马进行精心科学的饲养。只有吃得好,体质好,才能保证在战时,奔跑几十、上百公里还能冲锋陷阵。在国家粮食短缺,实行计划供应时,制定的标准仍是,每匹马每天5斤半口粮,即马料。这些马料主要是豌豆、黄豆、玉米、大麦、青稞等。我们连的马料都是隔一段时间,根据连队库存情况,借用分区后勤部的卡车,从州上的粮库里运回。每次给我们军马拉马料,都是连队的大事,装卸都由12个班的战士轮流担任。当时每个人都得扛上200斤重的麻袋,上上下下的搬运,虽然很辛苦,但为了我们的军马,大家都乐意干。
果洛每年的无霜期很短,只有四、五个月的时间,因此,我们都要抓紧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每天将全连的军马放到野外,让它们尽情的去吃鲜草。早饭前,我们解开马缰绳,由一名正副班长和每个排的一名战士负责,将成群的马儿,赶到十几公里外的山上,直到傍晚时分再全部赶回来。晚饭后,全连人员都到马厩外等候,军马回来后,每人将自己的军马套上笼头,带回马厩,将马料倒在马槽里,拌上一些咸盐供它们享用。吃完后,我们一般都会将军马拉到马厩外,用刮子或用刷子给马梳毛、刷背,为它们解乏、挠痒痒。我们也会摸摸它们的头,搂一搂它们的脖子,顺一顺尾巴。只有这时,才是我们和无言战友增加感情的极好机会。
果洛的九月份,草原上的青草都已经开始发黄、干枯了,这时候我们也就不能放马了,而是用从藏民手里买来的干草来喂养。为防止冬天军马体力下降,我们在夏季鲜草好的时候,每天给马匹尽量少喂一些马料,譬如二、三斤,冬天即增加到七、八斤,这样既保证了军马的身体健康,也使全年的马料数不会超额。
没有哪一个当兵的不怕半夜紧急集合,我们骑兵就更紧张了。步兵穿好衣服,打好背包,挎上枪就可出发,而我们不光要自己穿好衣服,还要将被褥装在马搭子里,带上各自的武器。我们排每个班配的是60炮,于是我们还要将炮身、炮架和护板分开由几个人分别背上,并带上各自的马鞍子、马料袋,朝几百米外的马厩里跑去,到了马厩里,凭感觉摸黑摸到自己的军马前,系好马鞍子、戴好马笼头,搭上马料袋和马搭子。冬天,我们怕铁质的马嚼口粘掉马舌头上的皮,还要边跑边将马嚼口放在我们的衣服里往热里暖。此外,每个班的口粮和炊具还要安放在身强力壮的公马上。一个班一匹公马,一般都使用骡子,它跑起来的速度虽然赶不上军马,但它力气却比马要大。出发后,由一名老兵或副班长拉上公马,同大家一起前进。所以,骑兵出发时,要做的事情的确不少。
外出野营拉练,快到中午或晚饭时,管伙食的副班长都要下马,找上一块牛粪捧在手里,随后点上一支烟,将牛粪引燃。待连长宣布做饭时,全班人员迅速跳下马来,新兵负责把全班的军马拉上在周围吃草,其他战士按照分工,有的找石头支锅,有的去河里提水,有的在小案板上和面,有的去周围捡拾干牛粪烧火,有的用火皮袋吹风助燃,待水开后,大家一起动手揪面片。面熟后,倒上葱花、调料和大肉罐头,便抓紧就餐。连长从下命令开始做饭起,一直都计算着各班时间,我记得做饭最快记录,也就是十七八分钟。有一次,连队赴拉加寺进行拉练,我们外出了三天,三天的狂风一刻也没停止。我们的头发里、耳朵里全部都是沙子,我们做的每一顿饭里,都混有沙子和牛粪,这样的饭,我们不吃也得吃。
我们爱军马,军马也熟悉我们。我在八班当新兵时,还被选拔担任了接兵连的文书,于1968年底,与我们的指导员、连长和几名排长一起到南京40多天,接回了六九年的新兵。我离开连队一个多月,回来的那天傍晚,我朝着马群老远打着口哨:“逗、逗、逗”。这时,我的军马竟然马上抬起头来,张望我许久,直到我跑过去搂住了它的脖子。这个情景至今难忘。
潘炜在执行任务途中
1969年,根据军委的命令,取消骑兵的建制,正式编制的骑兵部队全部撤销。位于甘南的骑三师、骑四师的身强力壮的马匹,按要求都留给周围的省军区所属部队继续使用。11月,我刚刚加入党组织,便被抽调参加了由我们独立连的副连长梁儒泉、副指导员李宝山和分区的兽医哈有德,带领我们七八个战士组成的接马队伍,一起前往甘南的合作县,去接分配给我们的军马。这些军马由于从来没有和我们接触过,十分生疏,所以有时也不听我们的话,调皮捣蛋的情况也会发生。记得往果洛返回的一天下午,100多匹军马在我们的带领和管护下,正在有序的前进。我那天走在最后,突然看见两匹马离开队伍,朝南边的山上跑去。我随即迅速的追了上去,其中的一匹,在我的呵斥下回到了队伍当中,而另一匹马就十分的任性了,我下马后朝它走去,我走几步,它向前走几步,我停下来,它也停下来不慌不忙的吃草,就跟没事一样。就这样,我们僵持了将近一个小时。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一个人是实在没有办法赶它回来了,只好先去追赶队伍。下到大路上,在一个帐篷门口,一个藏民小伙张开双臂挡住去路,向我呼喊:“哈喽,雪桶雪桶,糌粑唆!”(即喝酸奶,吃炒面),我知道,这是对我的友好表示,但我只身一人,又背着冲锋枪,我哪敢在此停留,只好说“脑、脑、脑”(不、不、不),便冲出“围挡”,赶大部队去了。由于在山上折腾的时间太长,一天又没有吃东西,走着走着马也乏了,走都走不动了。我只有骑上一会儿,下来拉它一会儿。天已全黑了,我也没走过这条路,分不清东西南北,在许多岔路口,我只有下马,仔细看着路上的马粪,哪边的多,就朝哪里走,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还好,循着马粪,我终于找到了部队宿营地。这时大家已经吃过晚饭,准备就寝了,我将丢马的事情告诉领导后,第二天派了两名战士原路返回,才将那匹马找了回来。
潘炜于1990年荣立三等功时的纪念照
1972年4月,我从独立连司务长的任上,调到了分区政治部保卫科。我们虽然在分区工作,但是只要机关干部下乡,除过去远的地方需要派车外,一般都是从独立连借马骑着下乡。有一次果洛州公安局接到民兵的报告,说发现从台湾飞到果洛上空的一只大型气球,在半空中自动打开了悬挂的木箱的箱门,大量的反动标语,以及半导体收音机、白砂糖包飘洒一地。分区领导指示我骑上军马到州上集合,带着民兵赶往事发地点。到了现场,只见方圆几公里的草原上,到处都能看到各式各样像邮票大小的纸片,上边印着标语,诸如:“学习陈胜吴广,推翻X共统治!”等内容。我们和民兵一起捡拾了多半天。后来由于散落的太多,又都隐藏在青草里,加之一般人也不会跑到这些偏僻的地方来,藏民大多也不认识这些字,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大,而就此作罢,收兵回营了。
在和平年代的大草原上,在交通极度不便的情况下,军马也为我们充当了很好的交通工具。1975年,全国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安排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活动要逐级传达。当年冬天,我们军分区也抽调了十几位参谋、干事、助理员和几位科长,一起参加了地方的宣传教育活动。我们这些人先被分配到各个公社和生产队,同当地藏族、汉族干部一起开展工作。我到了玛沁县的下大武公社第三生产队,和队长当周、副大队长嘎日多、公社武装干事土合曼、县农牧科干事班洛、县兽医站兽医青排一起,将129户牧民分成几个小组,每天骑上马轮流前去传达上级会议精神。我们还学习内蒙古“草库仑”的经验,把草地分成夏窝子和冬窝子(给冬天留上好草山,夏天让牛羊在较差的草原上放牧),我们和牧民一起,将石头从山上背到草库仑边,用石头垒成几十公分高的围墙,以阻挡牛羊的进入。
由于我们住在藏民帐房里,天天吃着糌粑,喝着酥油茶,分区领导怕我们受不了,于是将分区干部安排在一起,让我们自己做饭。这时我们又全部集中到了大武公社三大队。下乡后我一直努力地学习藏语,把藏语用汉字或俄语字母记录下来,共记了三小本的常用语。当时,我都能用简单的藏语与他们对话,拉家常了。在分区汇报时,分区政委孙经元对我学习藏语的成绩,还提出了表扬。当地牧民对我也十分喜欢,老乡们都亲切的叫我:“阿克潘炜”(潘炜叔叔)。直到现在,仍然有藏族群众还记得我这个“阿克潘炜”。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天都和自己心爱的军马为伴,由它载着我们走家串户、上山下乡。军马也是我们须臾不能离开的战友。我的骑兵生涯直到1976年底,离开果洛的下乡藏区,调到省军区政治部时为止。
人们都说,果洛不是人待的地方。我们的驻地海拔在3800米以上,空气稀薄,缺氧严重,无霜期极短,气候寒冷,青草只能生长一百来天。我们分区机关院子里,树木无法生存,只能种些大黄,作为绿色植物。这里的水烧到69度时,就开得哗啦哗啦的沸腾了。刚到果洛,我们从井里打上水,提着水桶走上十来步,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头昏眼花,喘上一会儿,才能继续行走。那时,冬天从内地接来的新兵,几乎年年都有因为感冒成了肺炎、肺气肿而丢了命的。我的十个手指甲也像许多人一样,中间连着肉,而指甲尖全部翘了起来,剥葱剥蒜时钻心地疼。我们冬天站岗时,每班要站两个小时,但我们穿着皮大衣和羊毛里子的皮大头鞋,只要半个小时,就冻得腿脚发麻,没有了知觉。内地的棉裤能穿四年,我们是骑兵,马裤屁股上的棉花,由于和马鞍子的摩擦,穿上一年就被蹭到了四周,剩下两层布,坐在哪里都十分冰冷。在果洛时,由于高原反应,食物煮不熟,大家消化不良,许多人从早到晚,肚子里边就像打鼓一样,气在里边窜上窜下。我在果洛服役几年,体重不但没有增加,还减少了十几斤,离开时已不到一百斤重。
我在果洛生活战斗了八年,虽然这里条件艰苦,但我依然感到很幸福,这是因为,这里是我为保卫祖国奉献的八年,是我享受骑兵生活的八年,也是我革命意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得到全面锻炼和树立的八年。
有了这八年极端的苦,才使我后来走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觉得什么困难,都不能和果洛的骑兵生涯相提并论,任何的苦,都不能叫做苦了。有了果洛的苦,才使我后面有了所向披靡的进步和发展。我要感谢我的骑兵生活!我要感谢世界屋脊,培养了我坚强的意志,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力量!这里,也给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骄傲,我曾经是高原骑兵!
2019 年 9 月 3 日定稿
作者简介:
潘炜,1948年11月生,西安市人,大学文化。从小酷爱书法。1987年进入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学习书法三年后,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高级班毕业。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中国金融书法家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市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西京大学客座教授、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客座教授、陕西长安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书法界泰斗吴三大先生入室弟子。军旅书法家。
西安网站建设杰商网发布